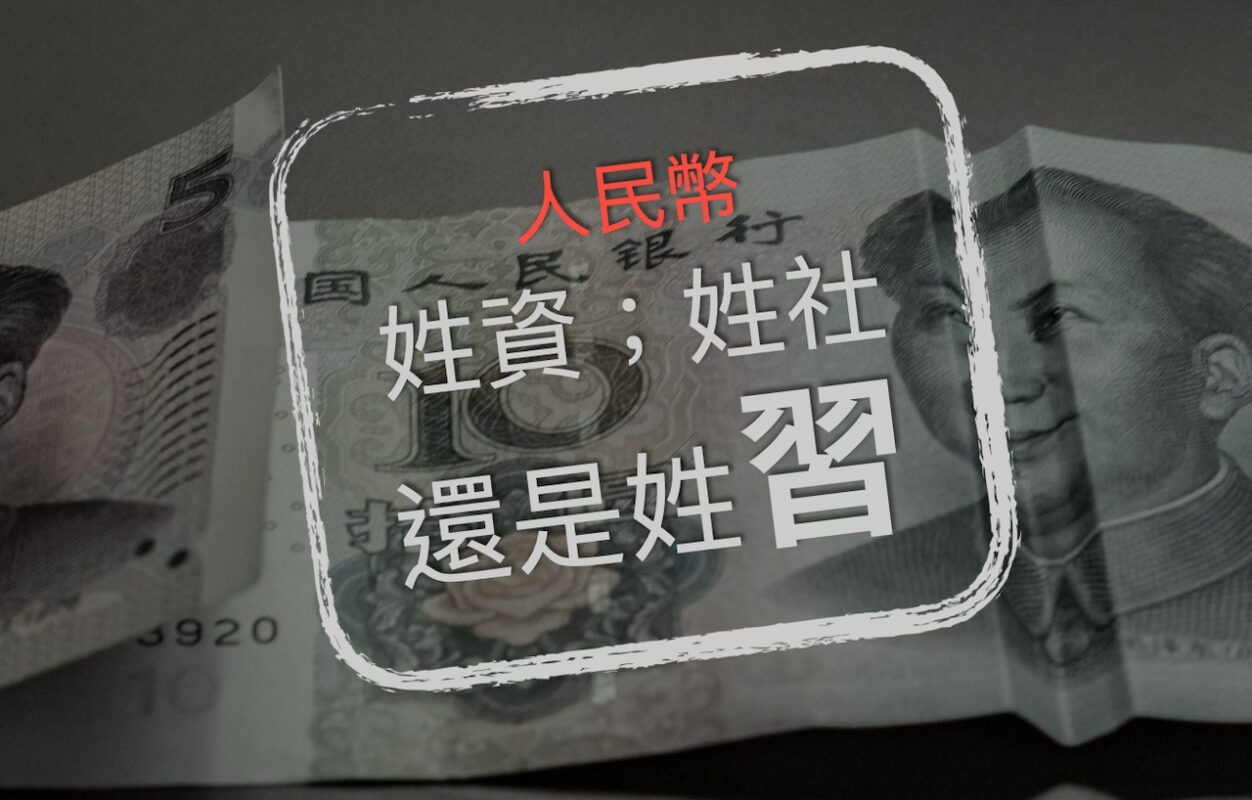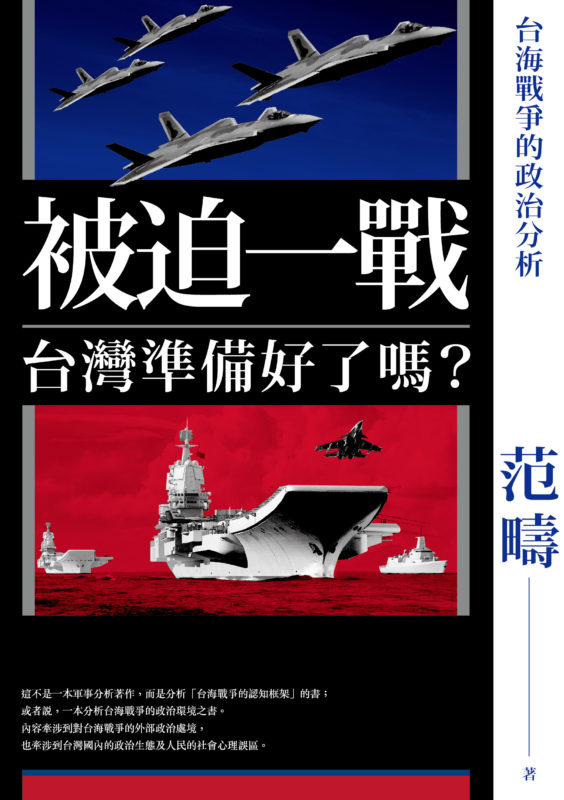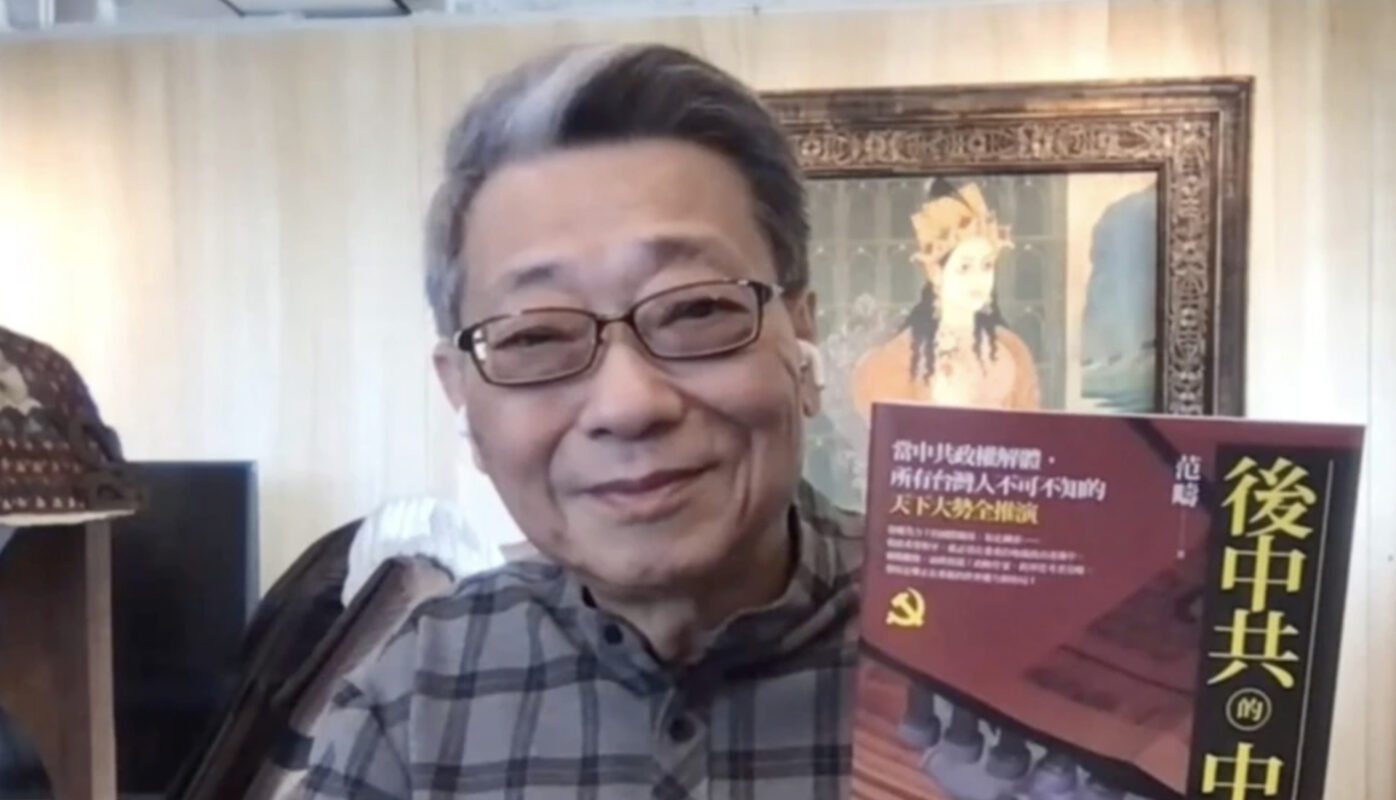80後的讀者可能不熟悉本文標題的表述,但你現在必須嘗試去明白——因為它牽涉到台灣經濟的未來,也包括了你的未來。
1950年代末期,由於毛澤東的經濟冒進,帶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,幾近亡國。中共內部無計可施,鄧小平等一幫人提出了經濟方向的「貓論」——管他黑貓白貓,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。毛澤東繼續亂搞,發動了「文化大革命」,長達十年,鬥倒了所有不同意他的人,又弄死了幾千萬人。「貓論派」全軍覆滅。
「改革開放」皆是假;「死不認錯」方為真
一直到1976毛澤東過世,文革結束,中國經濟離亡國只有一步之遙,全體共產黨人幾乎一致同意:只有「改革開放」才能避免中共解體、中國亡國。
然後問題來了。即使進行「改革開放」,應該走社會主義路線呢?還是走資本主義路線呢?這樣又吵了十幾年,主題就是中國的未來究竟是「姓社」還是「姓資」?
90年代初期,鄧小平再度祭出「貓論」一錘定音:管他姓社姓資;黑貓白貓——抓到老鼠就是好貓。當時主掌經濟的陳雲及一些其他老幹部都附和此說,於是波瀾壯闊的「改革開放」啟動。
鄧小平有他的奸詐,只說「讓一部份人、一部份地區先富裕起來」,把「然後呢?」這個問題留給了後人。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,本質上就是這個「然後呢?」未解問題的第一次爆發。鄧小平死後,後繼的江澤民、胡錦濤20年間,也都不敢碰觸「然後呢?」這個大哉問,只敢鼓勵大家「悶聲大發財」。
2012年胡錦濤面臨黨規的退場,繼承人有李克強、習近平兩個選擇。元老院最終選擇了紅二代的習近平,因為擔心李克強啟動真正的政治改革,動搖共產黨的一黨專政。
2012年像中共及中國的歷史拐點,但既是也不是。不是——因為其實1989年鄧小平等元老院選擇了坦克屠殺要求政治改革的青年,路線上就已經注定了2012年選擇紅二代接班。是——因為路線已經定在「保江山」,必須加強專制,而專制到底的結果一定就會出現「獨夫」。這——就是今天當下的情況。
中共專政七十餘年,無論其經濟路線如何折騰,姓資還是姓社,黑貓還是白貓,骨子裡貫穿期間的就靠三個條件:暴力、欺騙和供飯。前二者傳統上稱為「槍桿子、筆桿子」,新添的後者可稱為「錢袋子」,也就是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年間的「金融財政系統」。
無可避免當了獨夫的習近平,先收盡了天下的筆桿子,再收拾了所有的槍桿子、從陸軍到火箭軍到海軍,然後,兩週前他親自到人民銀行、外匯管理局「視察」,表示從今往後錢袋子的拉鍊開關也得聽他的。
緊接著,2023年十一月三日,中共「國家安全部」對金融系統發出信息:《一些居心叵測者妄圖興風作浪,警惕「看空者」、「做空者」、「唱空者」、「掏空者」》。要言不繁地說:這就相當於美國的CIA 加FBI 正式宣布接管「聯邦儲備局(Fed)的決策機制,每一塊錢的發行及流動都得聽習近平的。
台商被迫共產到底
錢袋子,自今往後,不再「姓資」、不再「姓社」,而是「姓習」!
中共政權正面臨經濟上的空前難關,但是三十年來民間累積的現金財富,根據經濟日報2023年2月21日的報導,《中國住戶存款餘額為126兆2000億元(人民幣),人均存款約8萬9400元,按一家3口算,中國每戶儲蓄不到30萬⋯⋯約當美國之1/4》。現在中共已經表明,這些錢都姓習。
前陣子謠傳,銀行存款在3000萬人民幣以上者,必須繳納20%給中共財庫。我相信,不久後這將變成遙遙領先的預言。
中共對鴻海集團(富士康/工業富聯)之資產沒收恐嚇,固然有郭台銘先生參選總統之因素,但我判斷真正的原因是習近平在算帳:台商在中國賺的每一塊錢,遲早都會直接或間接的返還中共,即使是對那些呼應統一的。
台灣應該立刻開始估算:上述事件發生時,台灣的總體經濟虧損。我個人從10年前開始就建議台灣投資中國的家族企業,在中資產讓出一半以上股權給美商或歐商,這樣當錢開始「姓黨」的時候才能保全。但沒有一家聽得進去。
現在,錢不但姓黨,而且還姓習了,這已經到了能逃多少算多少的一翻兩瞪眼時刻!